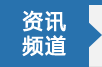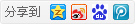为了陪来自刚果(金)的老乡Tanya买货,Felly起得比以往要早一些。3月14日的广州清晨,室外温度还不到20℃,Felly套上了他最喜欢的皮衣。
38岁的Felly经营一家跨国贸易公司已12年。办公室位于小北附近一栋破旧大楼的17楼,只有一个文员在帮他处理事务。自2003年第一次到中国,Felly的家和公司就安在了广州小北。
“小北——小非洲。当年小北比现在还要繁华,看到这里第一眼我就决定不走了。”Felly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来中国之前,Felly在刚果(金)做外贸生意。“我去过很多国家考察。有一天家人跟我说,为什么不去中国看一看,给自己一个机会?”
此前,Felly的叔叔早于2003年已经到广州做生意,收入还不错。Felly追随着叔叔的步伐来到广州,一待14年。他如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身份——刚果(金)在广州的民间大使。
每个非洲国家在广州都有一个民间大使,由在广州的本国人选举出来,对内负责处理纠纷、帮助本国人更好融入中国、举办社区活动等;对外要负责与当地的政府沟通。以刚果(金)的民间大使为例,这个职务一届三年,2017年要重新选举。
“选举的会议应该安排在我们国家国庆(6月30日)之后。”Felly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政府部门一直希望民间大使能管理好在广州的本国公民,此外他们还要承担联系和记录同胞的数量。
“现在在广州的刚果(金)人约500人。10年前,人数是现在的一倍多。”Felly说,2006年有1200多刚果(金)人在广州。
Felly知道广州刚果(金)人的大概人数,但广州乃至广东的非洲黑人人数到底有多少?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2017年3月,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交了一个提案——《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提案中称,据各方面大概统计(广东)已有50万“黑人口”,除合法入境者约2万以外,其余为非法入境或过期居留,带来一系列问题。
究竟“黑人口”人数几何?2017年3月5日,针对外国人“三非”(非法居留、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问题,广州市公安局在官方微信号“平安广州”上发布信息释疑。据统计,2016年经广州各口岸出入境外国人首次超过540万人次,达到541万人次。其中,入境的外国人269万人次(含非洲国家人员28.6万人次);出境的外国人272万人次(含非洲国家人员29万人次)。而非洲国家人员1.1万多人,约占实有外国人总数14%。
Felly和Tanya是其中合法进入中国的非洲商人之二。
一
Tanya 7年前到华南农业大学读研究生,如今在大连某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她的生意并没有离开广州。休假的十几天里,Tanya一直在广州看货,Felly陪同。
通常,Felly陪同逛街、介绍商家卖货是要收服务费的,这是他公司众多服务之一。
Felly和顺德几家家具厂的关系不错。他近日接到非洲朋友发来的沙发照片,请他代为询价。“沙发大概一万多元,我可能会收几个点的手续费。”不过,Felly没有收Tanya的逛街“陪伴费”。
他带Tanya去了流花市场。“流花市场很老了,是广州最早的批发市场之一。”Felly说,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流花服装批发市场开业于1996年,走的是外贸国际化的路线,多年来大量外国商人都聚集在此买货。
穿梭在这里,Felly如鱼得水。不管Tanya想买什么,Felly都能带她快速地找到合适的店铺。
走到流花批发市场中心区域的一家存活了十几年的档口,店里的员工纷纷和Felly打招呼。“Felly,你来啦?最近是名人啊,有那么多人找你?今天打算买什么?”
“我带朋友来买裤子。”
“随意挑,你知道价格的。”
Felly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一般他带去档口的客人,都会得到更优惠的价格。“而且,我不需要付定金。”这个“特殊待遇”足以让Felly感到骄傲。
这里,一条男士休闲裤的价格在一百元左右。Felly说,这价位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拿回非洲每条可以卖到两百元左右。但是十年前,这儿同样质量的货物价格只要五六十元,卖出的价格不会比现在少太多。
“以前可以挣到百分之百甚至更多的利润,现在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十几。”Felly总结说。
Felly和Tanya看好的货,通过空运寄回,一周之后就会出现在刚果(金)的市场上。Felly精于此道,他对界面新闻记者解释,服装是有流行期的,如果集装箱送回国,一般需要一个月,衣服过季的风险很大。选择空运只需一周左右。不过,以前空运32公斤的货物运费不超过100美元,现在同样重量的货物空运需要170-200美元。
非洲大多数国家缺乏工业,物资匮乏,当地市场严重依赖进口。采访中,有不少非洲商人这样调侃,“如果中国人不卖衣服,我们可能都没有衣服穿了。”
通过倒货挣差价,几乎是所有非洲商人共同的模式。此外,他们还会给在非洲的中国商人提供投资顾问、物流和仓储等服务。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教授从2009年开始研究在穗非洲人的课题。他认为,在中国的非洲商人,承担了经济和文化桥梁的作用,但他们仍然只是族裔经济,还是在非洲族裔内部的经济体系中运行,并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进入我们劳动力市场,成为我们的劳动力的数量几乎没有。但是对中国经济依然有好处。”

Felly陪Tanya挑选裤子。摄影:袁浔杰二
在穗非洲黑人的“广州梦”,和贸易有关。
始于1957年春季,一年两次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即广州交易会(下称广交会),让“广州贸易”声名在外。
1990年代,广东以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的“世界工厂”闻名,本地工厂通过低劳动力成本为全世界生产各种便宜的货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贸易转移的新契机,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经济严重受挫,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崛起,广东等沿海地区生产的货物在非洲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是早期吸引大量非洲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2002年是中非贸易的逐渐提升阶段。在此期间,非洲对中国出口由24.6亿美元上升至69.2亿美元,非洲从中国进口由14.2亿美元上升至54.3亿美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商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旧时利润高,他们会找人拼单,凑货物装满集装箱或者选择更快的空运。有时,寄一次货物就能挣到一两万元,有的商人通过“倒货”一年可以很轻松地赚一两百万元。
贸易形态催生了非洲人来广州淘金的梦。
非洲人越来越多,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越来越旺,小北在非洲人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广东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穗的非洲人数量增速远远快于其他国籍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在穗的非洲人口数量为6000人,2005年增长至20000人,年均增长率为33%。
人流带动物流,带来资金流。2003年起,中非贸易开始进入持续6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2008年,非洲对中国出口从83.6亿美元跃升至559.7亿美元,非洲从中国进口则由101.3亿美元上升至510.9亿美元。在此期间,非洲对中国贸易在2004-2006年以及2008年出现“顺差”,其中2008年顺差额最高达到48.8亿美元。2008年是条分界线。
在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影响下,2008年-2014年,非洲经济增速由2005年-2008年的5.83%下降到3.48%。
与此同时,中非贸易进入结构调整状态。2008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并延续至今。
Felly的生意经历了中非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也见证了在穗非洲人口的急速增长。
2014年,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广州外籍流动人口管理的现状分与对策研究》指出,广州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这些人主要集中在5个片区——小北、三元里、番禺、天河棠下和佛山黄岐。
小北是广州最早的非洲人聚集区,所以在很多非洲人的心里,小北才是广州的地标,有些人来到广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小北的登峰宾馆拍照留念。不仅是商人学生、游客,有些非洲的领导人千里迢迢到广州也一定要去小北。2015年12月底,津巴布韦环境部长Muchinguri一行到广州长隆参观项目。下午活动结束后,Muchinguri的女儿点名要去小北买礼物,长隆安排了一辆车陪着Muchinguri在小北逛街。
非洲人的聚集区主要以小北路和下塘西路为核心,周围几公里的范围都是非洲商人做生意的地方,这一带也有大量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餐饮店。
在三元里,非洲人聚集区主要沿广园西路两侧的批发市场、写字楼组成。这里主要是尼日利亚人,很多尼日利亚人在这里开了档口。
番禺的非洲人则主要集中在丽江花园和祈福新村附近,天河棠下和番禺情况类似,非洲人在此以居住为主。
佛山黄岐的情况比较特殊。在黄岐的非洲人也是以尼日利亚籍为主。由于黄岐地处广佛交界,离广园西路也不远,早期一部分尼日利亚人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住到黄岐,还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躲到两个城市的交界处。
大量的非洲人搬去黄岐,源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来的治安工作要求。彼时,广州对于“三非”人群的清查十分严格。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李志刚教授在其所著的《广州国际移民区的社会空间景观》中提到:“非洲移民开始采取逃离广州前往城市外围区域的方式,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2008年以后,居住在佛山的非洲人数量迅速增多。李志刚发现这些人群“大多属于非法移民或经济能力较低的移民”。
广州市公安局2014年数据显示,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约2000人,是在穗非洲人数最多的。其中常住人口近300人。该国也是被遣送出境的“三非”人员主要来源国之一,最近几年尼日利亚人有从广州转居佛山的趋势。

Felly自己试衣服。摄影:袁浔杰三
今年26岁的Artan,来自索马里兰。他有一个医生梦,“我从小就希望能帮助别人,觉得医生是一个不需要自己有很多钱,就可以帮助别人的工作。”
高中毕业后,Artan开始考虑留学的事情。他意识到,学医最好还是出国,非洲的医疗水平太差。“我考虑留学的国家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医疗水平要比我们好,第二是学费家里能负担得起。中国正好两个都符合。”Artan说,在索马里兰有一些中国商人从事矿产生意,他所了解的中国,都是索马里兰在中国留学的朋友告诉他的。在朋友的口中,“中国很好,一定要去看看。”
Artan第一次到中国的落脚点是武汉。他现在是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17年是他在中国的第7个年头。
在武汉读大学时Artan已经来过好几次广州。“我在小北有很多朋友,他们叫小北‘小非洲’,我也喜欢把小北称为‘小非洲’。”
每年放假Artan回到索马里兰,都有很多人问他关于中国的情况。“我们那还有很多人希望来中国留学,但是现在中国的签证政策变了,想来留学很难。他们只能等。”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下称新移民法)实施,管理趋严。外国人在中国生活,除了要有护照和签证外,还要随身携带居住证明。这几年在小北周边的小区,还能看到社区贴的提示,提醒外国人要随身携带相关证件,供警察查验。
由此带来对策的变化。有在穗非洲人表示,他们尽量减少用护照登记,这样警察就不容易追查到。一旦签证到期了被抓到遣送回国,就很难再回到中国了。
此外,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不少在穗非法停留的非洲人为了避免用护照登记被追查到,会和地下钱庄进行非法的交易。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表示,有些地下钱庄就躲在写字楼里,但是没有熟人引领很难了解到情况,“而且你并不是非洲人。”
非洲人为了留在中国做生意而取得合法身份,也愿意付出昂贵的代价。一般外国人来经商,需要中国的公司开邀请函。现在一张邀请函的价格最高已经被炒到两三千美元。
“我们的签证制度对于他们来说,过于严苛。当年我向监管部门提了相关建议,后来他们也有所改动。警方在执法时,就把非法移民分为恶意和非恶意,短期的非法滞留交罚款就可以了,不再像以前可能几年无法入境。”梁玉成说。
梁玉成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非法移民,来中国的前两三年是有合法身份的。
新移民法实施后,希望获得续签的商人必须先离开中国回到非洲,成本上升,获得续签的风险也提高了。当他们在中国的生意稳定后,有些人就干脆冒着法律风险“黑”在中国。
四
2008年,梁玉成去英国参加联合国会议,讨论的话题是50年以后的全球移民问题。
梁玉成说,长期以来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输出国,极大缓解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50年以后将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大量输入年轻人口,将和其他发达国家去世界上“抢”年轻人。
“这次会议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按照人口学的推演,中国有一天将会不得不引入移民,所以我觉得可预先做一些研究。”梁玉成回忆道。
2008年大量的非洲人已经开始在广州聚集,所以梁玉成采用受访者驱动抽样方法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方法专门研究隐藏群体和稀少群体,对这些群体进行抽样和大规模调查。在我的受访者中,近一半是非法居留的非洲人。”
2010年之前,从广州搬到黄岐的非洲人住在更靠近广州的江滨大道、黄岐步行街周边。但2010年广州亚运会后,佛山响应广州号召,也开始加强清查力度,并对非洲移民的小区进行频繁搜查。
李志刚指出,2010年中旬,大量的非洲移民离开佛山,为了避开警察,持有居留许可证的非洲移民则选择远离,去更隐秘的城中村居住。
2010年后,在黄岐,非洲人的聚集区躲进两公里外的北村和中村这两个城中村里。
但这并不是这些非洲人最终的落脚点。
2012年深圳大运会、2013年新移民法的实施、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的肆虐,每次大事件发生,相当一部分在穗非洲人都会更小心地躲藏起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知道同胞里有一些非法移民。“在不同的时候,被警察拦截的风险不同,通常凌晨、深夜以及午饭时间,是最安全的时候,此时警察少。”所以很多人选择早出晚归。
从2008年开始在黄岐开出租车的袁师傅经常搭载黑人乘客,他回忆称,“没有身份(签证)的非洲人是不敢坐公交和地铁的,他们一般三四个人拼一台出租车。早上从黄岐去广园西路,晚上九十点钟再回来。广园西路离黄岐不远,打车不会超过30元。”
晚上10点的黄岐镇泌冲村,非洲黑人的身影在街上逐渐增多。他们也经常在岐海苑对面的大排档吃夜宵喝啤酒。
根据梁玉成的研究,在2010年前后,在穗非洲人数量达到了近年来最高峰,估计当时的数量约有5万人(包括合法和非法居留人数),但是他没有透露合法与非法居留人数具体比例。在穗的非洲人中尼日利亚人占比最高,尼日利亚人中主要是伊博族人。
伊博族是尼日利亚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曾经想独立(比夫拉战争)但失败了,损失惨重。伊博人在其国内没有政治主导权,被赶到贫瘠的山区。但是伊博人很聪明,被称为“非洲的犹太人”,他们在全世界寻找商机做生意,大量迁居国外。
2010年前后,有专家统计在穗非洲人数量约为2.5万人(合法居留)。梁玉成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也正是这个2.5万的数字成为后来大家误解在穗非洲人数量的主要依据。因为按照发达国家社会学统计的算法,总移民数等于合法移民数乘以8。所以当年有研究者用2.5万乘以8,得出在穗非洲人总共有20万人,也对媒体说了这个数字。
“但是这种统计方法计算,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的警察相较于西方警察,执法权更大。比如,美国的非法移民走在街头,如果没有犯事一般警察不可以查他,但是在中国是可以的,所以中国的情况绝对不能乘以8。”梁玉成认为,这些年由于监管更为严格,出现了非法移民郊区化的情况。
非法移民一般就躲到周边的城市,或者城市监管的死角地带。广州是合法为主,佛山是非法为主,这种情况不光广州有,北京也有,很多非法移民居住在望京。非法移民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现状。

一到晚上,登峰宾馆门口人口攒动,这是大家认识朋友,交流信息的好地方。摄影:袁浔杰五
在穗非洲黑人的“广州梦”能否延续下去,和经济有关。
2014年,中非贸易迎来历史新高,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首次突破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5.5%。
但是2015年开始,基于非洲政治局势的动荡与石油价格的变化,中非间贸易额下降。很多非洲商人即使冒着违法的风险,也不愿意回国。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实际GDP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弱的,这主要是因为占地区GDP整体规模一半以上的两个最大经济体——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表现不佳。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是造成尼日利亚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
2015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为1790亿美元,同比下滑19.2%;201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为1491.2亿美元,同比下降16.6%。
从2014年广州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在穗的非洲人数量明显减少。数据显示,2014年,广州市居住外国人士11.8万人,常住6个月以上有4.7万人,临时来穗7.1万人。其中来自非洲国家的占14%,约1.6万人。
广州公安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广州市公安机关查处的“三非”外国人占来穗外国人总数的0.11%,其中非洲国家人员仅占18.9%;以2015年为例,广州警方共查处的“三非”外国人仅约占外国人总数的0.15%,其中42.7%为疏忽大意造成的轻微非法居留(10日以内)。通过深入治理,在穗外国人“三非”问题持续好转,自2015年开始,“三非”问题查处总量连续2年下降,特别是2016年查处人数同比大幅减少20.7%。
界面新闻记者发现,虽然2016年在穗非洲人数量比2014年少了5000多人,但是在穗非洲人数量占在穗外国人数量比例不变,仍然是14%。
有专家分析称,这说明在穗的外国人数量整体在减少,并不单单是非洲黑人的减少,主要还是跟政府的签证政策与国内经济转型有关。
Felly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从2014年前后就有很多人离开中国去其他地方找商机。他也曾犹豫过要不要离开中国,回家乡重新开始。但最近发现情况又变了,“广州梦”仍可继续,“我晚上去登峰宾馆,发现最近突然又有不少非洲人来了。应该又有新的商机。”
梁玉成分析称,首先,整个非洲政治经济出现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非洲经济不景气,移民数量开始减少。其次,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轻工业开始转型外移,许多非洲移民跟着产业的转移而转移。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现在在穗非洲人最多不超过3万人(包括合法居留和非法居留)。
梁玉成说,目前若能使非洲移民问题可控,从中国对非洲战略层面来说,一带一路、国际化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国内工业产能过剩,所以需要将过剩的产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输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需要非洲。另外非洲有我们所需的大量的原材料,将来也是我们的市场。”梁玉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