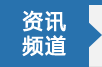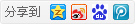图片来源:1 Granary
设计师奥利维尔·泰斯金斯(Olivier Theyskens)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21 岁时,这个黑发少年从布鲁塞尔知名时装学院辍学,在巴黎成立个人时装品牌,而后用家里的旧床单打造了个人的首个时装系列。在他的秀场上,哥特女孩身穿血迹斑斑的长裙,大踏步地行走在暗黑的室内,四周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和珠母贝砰砰裂开的声音。奥利维尔·泰斯金斯颠沛流离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整个行业云波诡谲的缩影:2002 年,正当奥利维尔的个人独立品牌无以为继的时候,奢侈品牌巴黎罗莎(Rochas)慧眼识珠,任命他为创意总监,不过后来巴黎罗莎的母公司宝洁(Procter & Gamble)认为继续保留公司旗下这个唯一的时装品牌不具优势,奥利维尔便转而投入莲娜·丽姿(Nina Ricci)的怀抱。可是在莲娜·丽姿工作了没几年,奥利维尔又被安德鲁·罗森(Andrew Rose)请到纽约担任 Theory 的创意总监,正是他为 Theory 定下了设计“给酷女孩穿的潮流服装”的调子。今年,奥利维尔的个人同名品牌再次起航,而这场暌违多年的时装秀以朴实无华、极简主义的空间为背景,致力于让时装自己说话。
奥利维尔在安特卫普 MoMu 时装博物馆为自己的展览《She Walks in Beauty》(她在美中行)做前期准备时,我对他进行了采访。和他的秀场一样,设计师本人也散发着一种沉静的气质。他穿着一身白衣,坐在空无一物的长桌旁,看上去已经准备好面对自己的过往了。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奥利维尔的言谈中饱含着激情,他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的经历分出个三六九等。不管是跟我解释高定时装的涵义,还是描述如何设计一件完美的夹克衫,他所追求的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
做展览为你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个契机。那么在你看来,你的职业生涯是什么样的?
我的职业生涯很有趣,不过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记得我刚入行时的环境跟现在很不一样。回顾过去是挺好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一定不要忘记,时代不同了,社会结构也不同了。当初我的思路跟现在不一样,当时的环境跟现在也不一样;人、能量也都不一样。这点特别关键,就是你回首过去,想到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不过同时意识到这代表的只是当时的我,而不是永远的我。我过去做的东西,以后可能不会再做了,不过以后我所做的东西里可能会带有以前那些东西的影子也说不定。说来挺好笑的,从 Theory 离职以后,我给自己放了一年假,决定收拾一下自己过去做的东西。我做了很多东西,但是它们都是装在盒子里,东一点、西一点,放得到处都是。我就想把它们都整理出来,然后妥善保存起来。我花了不少功夫给它们分门别类,这个工作真得是很累人,也很无聊。不过最后我还是做完了,当然有我朋友的帮忙。后来 MoMu 博物馆跟我谈合作的事情,我就想:谢天谢地,幸亏我已经整理出来了,现在要是让我把以前的东西都找出来,再分门别类地放好,我还真没时间。所以说,其实在做这个展览之前,我已经“回顾”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了,从 Theory 离职,离开纽约之后我就已经这么做了。
那在你回顾自己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意外的发现?
有些事还挺诡异的!举例而言,我给 Theory 设计的很多夹克衫,领子后面都带一个切口。所有夹克衫后面都有一个朝上的缺口,这样衣服的背面就很垂顺,很酷。我一直以为这个创意是我刚到 Theory 工作的时候想出来的,不过后来我整理自己过去设计的服装时,我才意识到早在做 2002 年春夏系列的时候,我就用过这个元素。我做的那个系列是受手套的启发。有些手套在手腕的部位不是有一个缺口嘛。然后我把这个设计元素转而应用到脖子后面,不过它们的视觉效果如出一辙。在纽约工作的那些年,我始终没把这个设计元素跟2002 年春夏系列联想到一起。照理说那个系列的衬衫、夹克衫、皮衣都用到了这个元素,我应该印象深刻才对。所以这就很诡异,就是我在完全不同的场合萌生了同一个创意:一次是受手套的启发,另一次是因为我想设计一款真正穿着舒适的夹克衫。我对以前作品的记忆都非常深刻,唯独不知怎地忘记了这个元素。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服装制作业。服装制作业在 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末的时候有了显著的发展。整个行业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注重细节。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发现当时的一些可能大部分人注意不到的技术工艺,那些由技艺精湛的工匠大师制作出来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你可以发现服装制作业的工艺在不断提升。
这跟技术的发展有关系吗?
服装制作工艺一直在不断进步。就拿给柔软的面料镶边来说吧,这就涉及到盖缝制的工艺了。1990 年代做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它跟现在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候做的东西很粗糙、很土,而且针脚很密、很大。
这真好。人们一般都认为服装的质量在不断下降,认为时装行业处在历史的低点。
这种看法恕我不能苟同。早在我到巴黎罗莎工作之前,我就已经在《A Magazine》工作很长时间了,我主要负责跟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借调历史服装然后组织拍摄。我跟他们借过迪奥(Dior)、雅克·格瑞菲(Jacques Griffe)和 老马萨尔·罗莎(Marcel Rochas)等设计的古着服装。在过去那个年代,设计师设计的服装都是由女裁缝师或者夫妻裁缝店来完成最后的制作,所以服装的制作工艺还是有一定保证的,绝不是粗制滥造。不过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因为它们源自以前那个年代,我就自顾自地以为它的制作工艺会更好,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古董衣中要想找到一件制作精美的服装真得很难。其实奢侈成衣品牌的制作工艺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不过有时候可能品牌对制作商在质量上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是让它们做快一点,对技术细节管理得不到位,所以让人们有一种服装的质量下降了的感觉。不过如果你想把服装做好,那么你现在做出来的质量肯定比 20 年前的要好。而且现在只要你敢想,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假设你想做一种特别的肩垫,那么你就可以联系日本厂家定制一款特别的肩垫。你想要最轻薄的面料,想要那种穿在身上几乎感觉不到的效果,也可以实现。现在的很多发明可以让你做出比以前更好的产品。
回顾职业生涯也意味着对整个行业进行反思。我知道你的工作是找到女士想要的东西。那么今天还是这样吗?有什么变化吗?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分辨什么才是女性想要的东西。我常常把自己代入到“女性”群体当中,想象女性会“喜欢这款衣服,想要那款衣服。想要尝试别的风格。”然后我奥利维尔本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女性满足她们的欲望。变化自然会有,因为你肯定不想重复自己。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也在不断演变 。有时候你可能会和信任的朋友聊上数小时,思考什么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你会不停地思索:“我在做什么?这样做对吗?这样处理会产生影响力吗?会有效果吗?”总之你会不断质疑自己是不是在做真实的自己。这一路走来我也经历了不少变化,我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我在过去所做的那些东西,即便我心里对它们还是抱着很欣赏的态度,也已经不是我现在想要的了。过去的那些东西放到现在完全不合理。有时候人们抱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希望我复制过去的作品,不过我真的不想那么做。我不会因为怀旧而复制过去。
你的变化在你的秀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你的第一场秀是在 1990 年代举办的,很遗憾我没有参加(奥利维尔笑了起来),不过我听说那场秀营造了强烈的戏剧化氛围,很有戏剧张力。而品牌重新启动后推出的时装展则以服装为主要焦点,秀场的装饰力求简约。这是你刻意而为的吗?
是的,因为那些东西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我了。有些元素很容易就会让设计师产生自我满足感,因为太十拿九稳了,双赢不在话下。用这些元素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小心。你必须敢于规避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举例而言,假设我非常喜欢一位音乐家,我很喜欢他 10 年前出的一张专辑,那么我可能以为自己会希望这位音乐家继续创作出相同风格的音乐,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这位音乐家不断重复自己,那么他的音乐除了复古以外别无新意,这就不对了。我们都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行。不过话说回来,做 2017 年春夏系列的时候,我并没有回避属于我个人特色的一些东西。比如,我在这个系列的服装里大量应用了钩眼扣(hook and eye,另有译作风纪扣,译注)元素。而我之所以会用到这种元素是因为它在我的设计作品中本来就很常见,好比我就是一个厨师,而钩眼扣就是我做菜时必不可少的佐料。
你花了一年的时间回顾自己过去的作品,然后说出这番话 ,还挺妙的。这么说来,这个整理的过程是让你更容易放下过去了吗?
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有时候你对这些东西的记忆是超现实的,结果就是你审视过去的时候会带上一层滤镜。而当你重新看到这些旧物的时候,你会想说:“还不错,不过我们当初的设计初衷是什么来着?”或许我当初应该更深入地探索一下我过去的作品,这样我就得出更好的认识。
这让我想起普鲁斯特的理论,他曾说只有透过一连串孤立的片刻以及这些片刻的总和才能正确评断一个人。
确实是这么回事。在回顾往期作品的过程中,当初自己曾有过的那些挣扎都历历在目。我能看到当初当出来的效果没有我预期得那么好的时候,我的那种沮丧和彷徨。事实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做出了裁剪精致、版型修身的夹克衫。我在 Theory 推出的夹克衫是我见过的第一件裁剪和版型都做到极致完美的夹克衫。以前我总是频频受阻。回顾过去的作品,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做的无数次尝试和无数次失败。很多系列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我不能再沿用过去的那些主题,所以只能讲一个全新的故事,让原来的那些主题就留在记忆的长河里,虽然有些系列并没有做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在这个回顾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当初本来可以把一些产品做得更好的。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趣,就是你在为其他时装屋和品牌设计衣服的时候也用到了你所说的“佐料”。那么我想知道你是如何透过其他时装屋或品牌来彰显自己的特性的?
有一些元素会不断出现在我的设计作品中。我不会称之为重复,它们很有我个人的特色,会不断重生,不断出现在我的作品里。这就好比说,我会对某一特定类型的女孩动心,有一种特定的感受或者样貌让我着迷,我喜欢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处理色彩和面料。回顾往期作品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家族渊源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妈妈是法国人,我继承了她的诺曼底血统,我父亲是比利时人,所以我骨子里又有比利时的民族精神。而这两种气质又是互相对抗的。它们都属于我,会追随我的一生。我之所以给那个模特穿黑色的衣服,不是因为她适合哥特风格,而是因为我觉得她很魅惑。还有那条白色长裙,我设计它不是因为自己喜欢婚纱,而是我觉得它很漂亮。这些元素会不断出现在我的作品里,我对它们欲罢不能。有一天我可能停止在设计中使用这些元素,不过几年之后,它们肯定会大张旗鼓地卷土重来,或者会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的作品中。这已经融入了我的 DNA。我不能看着自己的作品说,我要把“那幢建于 20 世纪的市长官邸已经从我的 DNA 中剥离了”,作为生命物质,我要不断进化。这些元素已经融入了我的表达体系,我必须接受它。
这方面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在非常纯净、朴实无华的场合举办 2017 年春夏系列时装展。因为这个系列的所有时装都代表了我最基本的设计主张,我当初想的是:这次就不要刻意躲藏了。在为其他品牌服务的时候,我把每个新的环境都看作是一个盒子,我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把盒子打开,彰显品牌的时尚理念,同时表达我自己的设计初衷。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风格和你自己的着装准则抛诸脑后。在莲娜·丽姿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当时刻意规避属于泰斯金斯的元素。不过现在我回过头去看,我发现我设计的那些衣服带有明显的泰斯金斯印记,而其实当我设计这些衣服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自己设计出的这些东西与以往完全不同,我设计的是完全不同,全新的东西。如果我是为其他品牌做设计的话,那么我设计出来的东西还会更不一样。现在回头看,我当初刻意抛弃自我,为其他品牌设计的服装却带有明显的自我印记,还蛮好笑的。
我对在“传统”品牌时装屋工作是什么情况特别感兴趣。你的职业生涯正好处在大型时装集团公司牵手新兴设计师的转折阶段。那么你可以解释一下传统意味着什么吗?
现在很多拥有光辉传统的时装屋都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他们全然推翻自己的传统,想跟它一刀两断。我刚到巴黎罗莎的时候,这家公司就处在这个阶段。尚蒂伊花边是巴黎罗莎的标志,当然是在以前,很久以前,而他们已经很久不在设计中使用这种元素了。只有公司推出的 Femme 香水的瓶身上还保留着这种元素。我当上创意总监以后跟公司说:“我已经看到有 10 个别的品牌在用马萨尔·罗莎设计的白底黑尚蒂伊花边,不过这个元素是属于你们的。不好意思,我们以后要在设计中大力使用这种元素。”对于一个品牌来说,有时候需要一个性格强硬的人来说一些不太中听的话。可能新的市场团队说了本季最流行的颜色是什么,不过他们说的不对。很遗憾,你给他们开的薪水很高,不过我来就是要否定不合理的东西。你既然雇佣了我,我就要告诉你事实。
那么你觉得市场营销团队不能做这么方面的决定?
能是能,不过有些品牌已经完全忘记了初心,他们不知道如何用好自己的传统,继往开来。结果就是他们聘请外部团队重新设计所有系列的服装。正因于此,这些公司需要聘请合适的人来为他们指引方向。如果香奈儿(Chanel)说:“以后设计的产品中都不要出现 CC 这个标志了,我们再也不想听到关于它的任何东西了”,那么 20 年后,所有人都会疑惑当初他们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标志。我到巴黎罗莎以后就是这么做的。我问:“为什么公司上下没有一件服装是跟传统挂钩的?”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棘手的地方就是历史资料很难找。我能找到的只有一本 1980 年代的黑白设计图册和几份内部档案。所以我只得自己琢磨他们的传统设计理念到底是什么。我还和伊莲娜·罗莎(Helène Rochas,马萨尔·罗莎的夫人,译注)以及巴黎几个熟悉这个品牌历史的人士探讨过这些东西。我就像一个调查员,追忆过去,畅想未来,设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当然有时候你也会想冒一点风险,所以你才会和朋友聊上几个小时,因为要考虑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说到综合多种设计理念,你很注重在高级时装和成衣之间保持平衡。我看了你早期的一些采访,我发现早在那个时候,你对时装行业的商业性就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不过你骨子里又有倾向于把时装当作艺术来对待。那么你如何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呢?
我觉得人们对高级时装(haute couture)这个词存在很大的误解。其中一个误解就是人们以为只有严格遵守一定规则做出来的服装才是高级时装。比如,你需要有一定的人手,制作的过程必须做到一丝不苟。不过高级时装设计师有时也会交出非常糟糕的设计作品,而与此同时,像加利亚诺(Galliano)等成衣设计师制作出了美轮美奂,如高级时装一般考究的服装。成衣品牌不断推出显然属于高级时装的服装,这让人们感到很困惑。不管是我自己,还是麦昆(McQueen)设计的成衣系列中,都包含具有高级时装感的服装。这些衣服你不会穿到大街上去,不过它们看上去真得非常漂亮,就像一件艺术品。而且设计上非常大胆,俨然已经属于超级概念化的范畴,就像维克托&罗夫(Viktor&Rolf)和川久保玲(Rei Kawakubo)一样。很多成衣设计师都在做纯粹的高级时装。对我来说,高级时装就是量身定做的服装。我量好你的尺寸,然后专门为你制作一件衣服,而且我所有的团队成员都会参与到这个制作过程中来,他们齐心协力服务的对象只有你。对我来说,这就是高级时装的含义。高级时装甚至也可能是一件T恤衫,只要有设计师和客户互动的过程,为客户量体裁衣做出来的衣服都是高级时装。
我一直在试图平衡这两者。比如你想出了一个袖型的设计方案。如果是制作实用的服装,那么你可以用这款袖型搭配简约主义的面料,效果就非常好;或者你可以把这个袖型和非常繁复精美的面料结合起来,把它制作成一件艺术品。作为创意工作者,你不能说,“现在我走这个路线,过会儿我走那个路线。”只要是合理的,你就应该尝试。在这个行业里你要和制作商一起合作,有的时候你提出来的要求会让所有人都很不舒服。水平高的制作商不难找,要想做到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也不难。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设计师太得寸进尺,提的要求太高的话,那么可能就会伤害制作商的利益。这个时候你需要认识到,你的设计方案很不负责任。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太恰当。所谓了解合作的对象,了解服装制作厂家,也就意味着了解他们的极限在哪儿。如果他们觉得你的想法不好,那么你就得调整自己的思路,换一种方式与他们合作。
我们聊聊你的工作方法。我知道你设计的第一步是画草图,那么你如何将二维的东西转化成三维的呢?
一般我画草图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三维的概念了。举例而言,虽然我画正面和背面的设计图稿要花很长时间,不过其实这个设计的背面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心里早就有数了。我一般是先从正面画起,不过有时候也会先画侧面,我是从看秀的观众角度出发。画完草图以后,我就给团队成员讲解我的设计方案,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然后我会进一步完善图稿,增加更多展示细节的素描。这一步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会跳过绘图这一步,从服装可穿性着手,自己直接动手剪裁。这种就是自然演进的办法了,跟绘图又很不一样。现在我又回到了最初的工作方式,先画出草图,然后再随着项目的深入进一步调整。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完美工作方式,因为我不喜欢不断重复同一个过程。在这次展览的图册目录中,我们收集了以前各个系列的草图。每一季的绘图都很不一样,因为我会调整画纸的版式,以及使用的工具。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无聊。
我已经看到你画的素描图了,每个系列的风格都很不一样,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画的都是行走的模特。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展览会命名为《She Walks in Beauty》(她在美中行)的一个原因。我在创作的工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的追求,即便有时候这会很不舒服。美是我的创作的一部分。不过我个人又觉得你觉得美的东西,可能在别人眼里很丑。我笔下的模特之所以都是动态的,是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营造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另外,它也能传达出我想要的衣服在模特身上飘动的效果,方便样板师打版。不过在展览的过程中,我们只能静态地展示这些服装,因为它们都很娇贵。不过在创作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它们动态的画面。
这就是时装展览会特别让人失望的地方:把动态的东西摆放收藏起来。
不过我们拥有巨大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衣服在动态的情况下是什么样子。比如我欣赏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法国大革命后被处以死刑,译注)在凡尔赛宫穿的一条裙子,如果只是纯粹观赏它的话,这件裙子看起来可能挺让人伤感的,不过如果你想象她穿着这条裙子在花园里散步,然后看过的电影就会一一在你的脑海里浮现。所以这时候就要充分发挥“脑补”的力量。现实当中,这条裙子其实已经破烂不堪了。前不久我刚看过迪奥的时装展览会,从历史的角度说他的作品会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这点我一点也不奇怪。即便从现在开始再过 1000 年,我们仍然需要他的作品,所以在处理这些衣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万分小心。
说到用想象力把这些服装封存起来,你的工作总是被大量的图片包围着,我在时装评论里看到过好几款你设计的服装的图片,比如那件罩衫裙。
我刚开始从事时装设计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所以给合作方寄图片就成了我们沟通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从职业生涯的早期开始,就保留下了大量照片,不是时装秀的照片,而是我为宣传和介绍时装系列而亲手制作的照片。当时,可以说我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制作这些照片上了。那个时候的人们对细节都很一丝不苟。我记得那时我会买《Italian Vogue》和《The Face》,放在书桌上,一看就是一个月。它们就是我这一个月的图片食粮,然后新的一期杂志出来后,我再买新的。现在想想还挺匪夷所思的,当时的我总是盼望着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不像现在,我们都被淹没在巨大的信息洪流里了。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在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些照片比现在拍出来的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那个年代照片留下印记的空间更大。展品目录里登记的很多资料都来自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觉得它们更有意思。这些照片里蕴含着很多未来的信息。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经营自己的公司的?有没有试着控制规模,就像刚起步时那样组建小团队?
时尚业改变得太多,我没法再走以前的老路了。重新推出自主品牌时,我其实并不清楚多大规模才合适。我只是觉得应该一步一个脚印,而且最好每天都能和同事碰面。要是能把精力放在这些问题上面,小团队也能做成很多事。从Theory离职之后,我很难想象在人手不足40人的团队中工作。不过后来我休息了一年,专注做自己的事儿,反倒希望跟小团队合作了。这样我就能和每个成员保持沟通,就像一家人一样。大家都非常投入,而且当年品牌还在起步阶段时就有参与,这点很重要。我们还在不断进步,日后也许会扩大规模,但目前团队人数不多,和我合作的都是些老朋友。长远来看,世界各地参与我们项目的人或许会有很多,但巴黎总部的核心成员只有少数几个人。
你在设计学院念书时,没有拿到学位就退学了。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去坎布雷念书,后来又为什么会决定退学?
(在学校里)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缝纫机有上下两股线(笑)。小时候我都是靠手工缝的,母亲踩缝纫机的时候我就总在旁边看着。我做梦都想试一试,但她每次用完都会把下股线轴拿下来。等到我偷偷用缝纫机的时候,上股线头穿来穿去,布片却缝不起来。我(到了 18 岁)才搞明白这个原理。在艺术院校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以前念的学校都很传统、很无聊,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和拉丁文。但在坎布雷,我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同性恋、怪人,还有设计师,我对他们很感兴趣。其中有几个同学和我特别投缘,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
第一学年还挺有意思的,第二学年我开始做兼职,不像之前那么专心学业了。到了第三年,我本性爆发,再也不想继续念书了。那时候挺冲动的,觉得自己受够了,所以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打算退学后继续自学。因为个性的缘故,我不喜欢和同学一起坐在教室里,做着同样的事,让教授来评判我的表现。这不符合我的天性。倒不是说建议大家都退学,而是说我希望摆脱那种教育模式。我有我自己的风格,不想受他人影响。学校没有做错什么,只不过 19 岁的我产生了这种想法罢了。我想成为一张白纸,设计我眼中的好作品,而不被他人观点所左右。退学后,我就设计了自己的第一个系列“1998 年春夏系列”,而且一点也没受到别人风格的影响。离开学校时,我唯一惦记的就是自己的作品。
我试着去实习,比如有一次带着一摞素描画去 Jean-Paul Gaultier 那儿应聘,前台的女士对我说:“把它们留在这儿好了,我们会给你回音的。”我当时就想:“我怎么能把它们留在这儿,那里面都是我的创意啊!”于是我就走了。我决定设计自己的作品。
你一离开学校就创办了自己的品牌,当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一切都水到渠成。时尚行业要求各个品牌都有组织、有条理,确保产品能顺利交付。这就是我当年面临的挑战。刚开始,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合理的生产模式,至少不能太糟糕。第一年里,我常常在采购员和记者面前演戏,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做不到即刻交付的,于是我就请他们再等一季。我很小心,不敢花太多的钱。我用的面料都是家里本来就有的,比如旧亚麻布匹和旧花边之类。我觉得那时候的采购员更宽容。要是刚出道的设计师做不到马上交付,或者生产的服装不够完美,他们也能够理解。如今,这种宽容已经不复存在了,业内能接受瑕疵的采购员也越来越少。我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完美,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当时的工作。还有不少重量级的演员为我做商业宣传,帮了我很大的忙。所以说,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让公司变得有条理,也许绝大多数年轻设计师都过不了这一关吧。我从身边人那儿得到了许多帮助,比如一位商学院的朋友就非常热心。你应该时时看看周围,想一想有谁能帮得上忙。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点非常重要。你要和人分享自己的目标、考虑和别人一起合作。单枪匹马的话,你是不会成功的——你只会感到疲惫。你还得明白,很多时候这份工作和设计无关。你要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支付账单等等,而且容不得你犯错。要是缺乏条理,公司就很可能会失败。
你刚出道时很受媒体关注,还有一些名人出面为你做宣传。这些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我觉得这在当时对我很重要,但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人人都会接触各种媒体,吸收大量的信息。要是回到 1990 年代,想给别人看你的作品的话,就得收发传真或者当面展示。想当年,只要能得到伊莎贝拉‧布罗(Isabella Blow)等名流编辑的支持,让你的作品登上《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封面,业内人士就会注意到你,他们还会来看你的展示或者到展厅里来参观。不过如今一切变了。当年还有少数几位采购员、记者在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我相信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
你曾经为学校做过几次评委,有遇到过像你一样的学生吗?有没有学生不需要接受学校教育就能培养自己的风格?还是说这种人很少见?
不好说吧。有些人有当伯乐的天赋。我给学生做评委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平时不太一样。我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称不上是专家。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是登在 The Face 杂志上的一小张照片。杂志一出版就有个意大利星探联系了我。英国设计师麦昆最早就是他挖掘的,安‧迪穆拉米斯特(Ann Demeulemeester)和德赖斯‧范诺顿(Dries Van Noten)等许多比利时设计师的成名也要归功于他。他会帮像我这样的年轻设计师联系生产厂家,还教会了我什么时候应该小心提防、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他在我身边真的很关键,因为他既能发现人才,又了解这个行业。他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宝贵,我到现在还是很感谢他的指导。毕竟,刚离开学校的人不可能马上就领会时尚行业的诀窍,需要过来人点拨才行。
最后一个问题。采访中,我似乎发现你离开学校后并没有停下学习。比如你提到曾在 Theory 学习裁剪那件完美的定制夹克。你有没有在哪个时间段里,发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表达创意了?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抵达最高境界并永远保持那个水平,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真的做不到。有时候你似乎觉得可以停下来休息了,可过了一年又有了新的项目,仍旧得重新开始学习。我在巴黎罗莎工作时,确实有过驾轻就熟的感觉。但我总觉得一直有新的知识等我去学,因为我的个性如此。也许别人会满足于现状,但我认为这样很无聊,我不喜欢这样。重新推出了我的自主品牌后,我开始设计自己的经典系列,感觉似乎已经小有建树。以我的天性,我会不停地寻找新的项目。这就是人生,不尝试新事物就会觉得无聊。
作者:Aya Noël